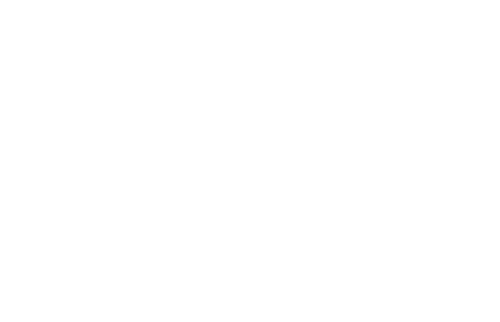梦的解释:众说纺纭(2)
2023-08-06 09:03:35
梦的解释:众说纺纭(2)的寓意好不好?暗示什么意思?代表象征什么?请看下面梦的解释:众说纺纭(2)的梦境详解:
醒梦皆虚幻
古印度人关于梦的观点是十分独特的,他们认为梦可以成为我们所在的物质世界中的现实,而同时,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本质上不过是个虚幻的梦。换句话说,梦像现实一样真实,而所谓真实的现实世界像梦一样虚幻。印度人认为梦和“现实世界”没有本质区别。印度的梦观和中国或其他民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上述中国古代或印地安人的信仰认为,梦是灵魂经历的“真实事件”,和现实生活一样是真实的。某和尚做梦时脑袋顶出来的蛇形的灵魂实际存在,并且确实吃过唾液,过了小沟;去了花丛。而印度人则认为梦和“现实”世界虽然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却都不是真实的,梦是虚幻,“现实”也同样是虚幻,没有什么“真实事件”在发生。
印度经典里有许多关于一个人在梦里变成另一个人的故事,而且故事中他们醒来后,发现梦中的事都是实有其事的。《婆喜史多瑜咖》中,有一个这样的特异的梦的故事。
在北旁多瓦的繁华国家里,有一个叫作拉瓦罗的仁慈的国王,他生于高贵的何梨坎多家族。一天,一个魔法师向国王鞠躬并且说:“陛下,您坐在王位上瞧瞧这种奇妙的把戏吧。”魔法师挥动他的孔誉羽毛的魔杖,一个来自信德的人造来了,牵着一匹马;当国王盯着那匹马时,他仍然在他的王位上呆着不动,他的目光呆滞,就像陷入了沉思。他的朝臣很担忧,但他们仍然保持沉默。凡分钟后,国王醒来了,从他的王位上掉了下来。他跌倒时仆人们连忙扶住他,国王迷惑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谁的宫殿?”直到他最终恢复感觉后,他讲了这个故事:“我骑在马上瞧着魔法师挥动的魔杖。我产生了骑在马上独自出去打猎的幻觉。走了好远,我到了一个大沙漠,穿过沙漠到达一片丛林,在树下一只爬山虎袭击了我,我的臂膀挂到了树上。我挂在那里,马从我下面走过去了。我在树上呆了一晚,没有睡觉,感到恐怖。我挨到第二天,看见一个黑皮肤的年轻女子拿着盛食物的坛子,因为我很俄,我请她给我点吃的。她告诉我她是个贱民,说假如我娶她,她便给我食物。我同意了,在她给了我食物后,她把我带回了她的村庄,我在那里同她结了婚,咸了一个收养的贱民。
“她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同她在那里过了6年,穿着发臭的、发霉和长满虮虱的缠布衣喝着我杀死的仍带微温的野兽的血,吃着火葬场地上的腐肉。虽然我是王父唯一的儿子,但我老了,头发灰白,衣衫褴褛,我忘记了我是位国王;我越来越坚信我是个贱民。一天,当一场可怕的饥荒。一场巨大的干旱和森林大火发生时,我带我的家眷逃进了另一片森林。我妻子醒着时,我对我的小儿子说:
‘来烤我的肉吃。’他同意了,这是他维持生命的唯一希望。
我被肢解了,当他预备好了烤我的肉用的柴堆,正要把我抛进柴堆时,在这要害的时刻,我,这个国王从王位上掉下来了。于是我被。‘好哇!好哇!’音乐般的呼喊声所惊醒。这是魔法师给我编制的幻觉。”当国王拉瓦罗讲完这个故事时,魔法师忽然消失了。于是朝臣们都惊愕得睁大了他们的眼睛,说:“天呀,这不是魔术师;这是神的幻觉,使我们熟悉到物质世界纯粹是个精神幻象。”国王预备第二天真的去沙漠,决心去再次找到那他精神意象中反映的不毛之地。他与他大臣们一道,沿途跋涉直到找到一块和他梦中所见到的一样巨大的沙漠,使他惊异的是,他发现了所有他梦见过的事物:他熟悉了他曾是他的熟人的贱民猎手,他找到了那个收养他为贱民的村庄。看到了这个与那个男子。女子,所有人们使用的东西,干旱袭击过的树林,失去父母的猎手的孩子。他见到了曾是他岳母的老妇人。他问她:“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是谁?”她给他讲了个故事:一位国王来这里同她的女儿结了婚,他们有了孩子,后来国为干旱,全村人都死光了。国王十分惊愕,满是怜悯。他问了更多的问题,她的回答陡他确信,这个女人所讲述的正是他当贱民时经历的故事。于是,他回到了城市和他的王宫,人们在那里欢迎他的回来。
从这样的梦的故事里,印度人引出了他们特有的梦观和世界观。上述经典中,在讲完拉瓦罗的梦和经历后,婆喜史多解释说:
“无知引起这一切,以致没有发生的事发生了,如一个人梦见他自己死了。精神确实经历了它本身所引发的事情,尽管这种事情并不真正存在;另一方面,它们也并非不真实。贱民村所发生的对国王拉瓦罗来说表现为他精神中的意象,它们既是真实的也是不真实的,或者是拉瓦罗直接看到的幻象变成了贱民精神中的一种意识的感知。拉瓦罗的意象浸入了贱民的心灵。因为正像相当相近的语言出现在许多人的心灵中一样,同样类似的时间。空间甚至行为也出现在许多人的心中,正如在梦里。正像心灵能忘掉所发生的一切,无论什么重要之事。同样,人们能确切地把某些事记忆为发生了的,即使它并没有发生。”
在印度的观念中,没有什么“现实的事件”,人的精神在梦中,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事件,对他的精神来说,是的确发生了。而且不同的人的精神意识或心灵中会出现同一个事件,仿佛大家同做一个梦,这种情况下大家就都认为这种事是发生过的真事而不是虚幻的梦。这种观点显然不是唯物主义的。
印度人的这种观点,在中国不是主流,只有庄子曾有过,庄子说:“我曾梦见自己是蝴蝶,醒来后想,是庄周做梦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成了庄周呢。”另一个印度人讲的梦故事仿佛正是为了回答庄周而讲的:
从前,有个喜欢想象千奇百怪的事情的僧侣。他所有时间都在冥思苦想,岁月飞快地逝去了。一天,一个幻念忽然袭击了他:“真有趣,我将经历发生在初民身上的事情。”他一有了这念头,他便莫名其妙地换上了另外一个人的模样,那人的身份和姓名,即使这只是精神造成的。由于纯粹偶然的事件,当一只乌鸦碰巧在树下,一颗棕树的果子掉下来刚好打在他头上时,他想:“我是吉婆陀。”这位梦者吉婆陀在一个梦构成的城镇里尽情地享乐了很长时问。他在那里喝得大多,倒下来沉重地睡着了,他在梦里看见一个整天读着什么的婆罗门,一天,那婆罗门躺下睡着了,整日的劳作使他很困倦,但那些日常活动仍然使他显得有活力。同样如此,在梦中他把自己看成了王子。一天,那位王子在饱食肉宴后睡着了,在梦中他把自己看作统治着宽广领地的穷奢极欲的国王。一天这位国工因为狼吞虎咽。纵情享乐而睡去了。在梦中他把自己看作是位仙女,这位仙女固连续的作爱的困倦而睡去了,她在梦里把自己看作一只有闪亮眼睛的雌鹿。一夭雌鹿睡着了,她梦见她是株葡萄藤,因为她从来就喜欢吃葡萄;就动物而言,它们总是记得它们所见所闻的东西。葡萄藤把自己看作在藤上酿蜜的蜜蜂;蜜蜂在莲塘里爱上了莲花/一天,官变得如此地沉醉子所仗用的莲汁,以致它的头脑都麻木了,正在此时,一头象来到塘边,踏翻了莲丛,仍然依附在莲上的蜜蜂被压挤而到了象牙上。当蜜蜂瞧着大象时,它把自己看成了发情期的大象,大象掉入了一个很深的陷阱,成了一头令人喜爱的王室的象。一天,象在战斗中被利剑砍咸了碎片,当它走向它最终的慈息之地时,它看见一群蜜蜂萦绕在从它的头脑上流出的甜美的血液上,于是象再变成了蜜蜂,蜜蜂又回到了莲塘,被踏在象脚下,这时它看到了池塘中它旁边的一只鹅。于是它变成了鹅。这只鹉在一段长时问里经历了数次再生,直到一夭,当它是一群鹅中的一只时,它熟悉到,作为一只鹅,它类似于梵天的天鹅,类似于造物主的天鹅,它一旦有了这念头,它被猎人射中死去了,于是,它再生为梵天的天鹅。
一天,天鹅见到了楼陀罗神,突如其来地,它想到:
“我是楼陀罗。”这个念头马上像镜中的意象一样反射出来了,它换了楼陀罗的模样。这位楼陀罗沉溺于他精神的每一种快乐,他生活在楼陀罗的宫殿,备受楼陀罗的仆人照料。
但是,这个变化而咸的搂陀罗有一种非凡的熟悉力,他的精神能看到他先前的每一个经历。他惊奇地看到他做了1oo个梦,他自言自语道:“多奇妙啊!这个复杂的幻觉愚弄了众人;非真实之物似乎是真实的,就像终归是幻境的沙漠中的水。我是某些能被想到的某物,我被想到过。在这里偶然碰巧地,在某个宇宙中有个变成了憎侣的灵魂,他经历了他所想要经历的东西:也变成了吉婆陀。但因为吉婆陀欣羡婆罗门,他把自己看作了婆罗门;因为婆罗门总是想当王子,他变成了王子。因为王子为了治理王国而想干番事业,他变成了国王;因为国王想满足淫欲,他变咸了仙女。变幻无常的仙女大妒忌雌鹿漂亮的眼睛了,她变成了雌鹿;雌鹿把自己看作她关注的依附男人的女子,女子把自己看作她观察了相当长时间的蜜蜂,蜜蜂被踩在他所看到了的大象的脚下,他时隐时现地经历了一系列的再生。一百次循环再生的结局是楼陀罗,我是搂陀罗,我是他。他站在再生的潮流中,在那里众人被他的精神所耍弄。就我的爱好而言,我要唤醒所有那些是我的再生的造物,我要观察他们,给予他们真正观测事物的能力,我要使他们联合为一。”
楼陀罗下了这个决心,他去了那个僧侣正像死尸般睡在寺院里的庙字。把他的精神投入僧侣的心灵后,楼陀罗使他醒来了;于是,僧侣熟悉到了他所产生的错误(即相信他的吉婆陀那样的生活是真实的)。当僧侣瞧着搂陀罗时,发现楼陀罗本是僧侣,也是吉婆陀及其他人造成的,他大为惊愕,尽管那个真正醒悟了的人没有发现他惊愕的原因。于是,楼陀罗和僧侣两人一块去了吉婆陀再生的精神角落的某个确实的地方,于是他们看见了吉婆陀睡在那里,毫无意义,手中还握着剑;那是吉婆陀的尸体。当他们的精神熔入他的心灵后,他们使他醒来了,于是,虽然他们是一个,但他们有三个形式:楼陀罗、吉姿陀和僧侣。虽然他们醒着,但又似乎没有醒;他们很惊异,然而又不惊异,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那里,像画在画片上的意象。
然后,他们三人在空中互相回应,飞越天空去了个地方,那是婆罗门的再生之地,他们在他家里看到了婆罗门,他与他妻子睡着了,他妻子用手挽住他的脖子。他们把他们的精神溶入了他的心灵,使他醒来了,他们全站在那里,不胜惊奇。然后他们去了国王再生的地方,他们用他们的精神唤醒了他,然后他们又漫游于其他人的再生地,直到他们到达了梵天的天鹅的再生处,在那时他们全联合起来了,变成了楼陀罗,一百个楼陀罗变成了一个。
于是,他们都被楼陀罗唤醒了,他们都欣喜兴奋,彼此观看他们的再生,观看如此发生的幻觉。然后,楼陀罗说:
“现在,回到你们的位置上去吧,在那里与你们的家庭共享欢乐吧,到时再到我这里来。到世界未日,我们所有人的,这帮无非是我的部分的造物都将走向最后的慈息之地。”于是,楼陀罗消失了,吉婆陀。婆罗门及所有其他的人都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与家人团聚,但一段时间后,他们将耗尽他们的体力,重新回来在楼陀罗的世界里团聚。
由引可见,印度人对梦的看法是最神秘的,他们认为世界就是梦。而梦中的一个人的精神可以转化或分解为几个不同的精神。这些不同的精神之间又是同一的又是独立的。这种观点比中国古人认为人睡后有一个灵魂出窍形成梦或鬼神致梦显然要奇异得多,神秘得多。
醒梦皆虚幻
古印度人关于梦的观点是十分独特的,他们认为梦可以成为我们所在的物质世界中的现实,而同时,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本质上不过是个虚幻的梦。换句话说,梦像现实一样真实,而所谓真实的现实世界像梦一样虚幻。印度人认为梦和“现实世界”没有本质区别。印度的梦观和中国或其他民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上述中国古代或印地安人的信仰认为,梦是灵魂经历的“真实事件”,和现实生活一样是真实的。某和尚做梦时脑袋顶出来的蛇形的灵魂实际存在,并且确实吃过唾液,过了小沟;去了花丛。而印度人则认为梦和“现实”世界虽然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却都不是真实的,梦是虚幻,“现实”也同样是虚幻,没有什么“真实事件”在发生。
印度经典里有许多关于一个人在梦里变成另一个人的故事,而且故事中他们醒来后,发现梦中的事都是实有其事的。《婆喜史多瑜咖》中,有一个这样的特异的梦的故事。
在北旁多瓦的繁华国家里,有一个叫作拉瓦罗的仁慈的国王,他生于高贵的何梨坎多家族。一天,一个魔法师向国王鞠躬并且说:“陛下,您坐在王位上瞧瞧这种奇妙的把戏吧。”魔法师挥动他的孔誉羽毛的魔杖,一个来自信德的人造来了,牵着一匹马;当国王盯着那匹马时,他仍然在他的王位上呆着不动,他的目光呆滞,就像陷入了沉思。他的朝臣很担忧,但他们仍然保持沉默。凡分钟后,国王醒来了,从他的王位上掉了下来。他跌倒时仆人们连忙扶住他,国王迷惑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谁的宫殿?”直到他最终恢复感觉后,他讲了这个故事:“我骑在马上瞧着魔法师挥动的魔杖。我产生了骑在马上独自出去打猎的幻觉。走了好远,我到了一个大沙漠,穿过沙漠到达一片丛林,在树下一只爬山虎袭击了我,我的臂膀挂到了树上。我挂在那里,马从我下面走过去了。我在树上呆了一晚,没有睡觉,感到恐怖。我挨到第二天,看见一个黑皮肤的年轻女子拿着盛食物的坛子,因为我很俄,我请她给我点吃的。她告诉我她是个贱民,说假如我娶她,她便给我食物。我同意了,在她给了我食物后,她把我带回了她的村庄,我在那里同她结了婚,咸了一个收养的贱民。
“她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同她在那里过了6年,穿着发臭的、发霉和长满虮虱的缠布衣喝着我杀死的仍带微温的野兽的血,吃着火葬场地上的腐肉。虽然我是王父唯一的儿子,但我老了,头发灰白,衣衫褴褛,我忘记了我是位国王;我越来越坚信我是个贱民。一天,当一场可怕的饥荒。一场巨大的干旱和森林大火发生时,我带我的家眷逃进了另一片森林。我妻子醒着时,我对我的小儿子说:
‘来烤我的肉吃。’他同意了,这是他维持生命的唯一希望。
我被肢解了,当他预备好了烤我的肉用的柴堆,正要把我抛进柴堆时,在这要害的时刻,我,这个国王从王位上掉下来了。于是我被。‘好哇!好哇!’音乐般的呼喊声所惊醒。这是魔法师给我编制的幻觉。”当国王拉瓦罗讲完这个故事时,魔法师忽然消失了。于是朝臣们都惊愕得睁大了他们的眼睛,说:“天呀,这不是魔术师;这是神的幻觉,使我们熟悉到物质世界纯粹是个精神幻象。”国王预备第二天真的去沙漠,决心去再次找到那他精神意象中反映的不毛之地。他与他大臣们一道,沿途跋涉直到找到一块和他梦中所见到的一样巨大的沙漠,使他惊异的是,他发现了所有他梦见过的事物:他熟悉了他曾是他的熟人的贱民猎手,他找到了那个收养他为贱民的村庄。看到了这个与那个男子。女子,所有人们使用的东西,干旱袭击过的树林,失去父母的猎手的孩子。他见到了曾是他岳母的老妇人。他问她:“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是谁?”她给他讲了个故事:一位国王来这里同她的女儿结了婚,他们有了孩子,后来国为干旱,全村人都死光了。国王十分惊愕,满是怜悯。他问了更多的问题,她的回答陡他确信,这个女人所讲述的正是他当贱民时经历的故事。于是,他回到了城市和他的王宫,人们在那里欢迎他的回来。
从这样的梦的故事里,印度人引出了他们特有的梦观和世界观。上述经典中,在讲完拉瓦罗的梦和经历后,婆喜史多解释说:
“无知引起这一切,以致没有发生的事发生了,如一个人梦见他自己死了。精神确实经历了它本身所引发的事情,尽管这种事情并不真正存在;另一方面,它们也并非不真实。贱民村所发生的对国王拉瓦罗来说表现为他精神中的意象,它们既是真实的也是不真实的,或者是拉瓦罗直接看到的幻象变成了贱民精神中的一种意识的感知。拉瓦罗的意象浸入了贱民的心灵。因为正像相当相近的语言出现在许多人的心灵中一样,同样类似的时间。空间甚至行为也出现在许多人的心中,正如在梦里。正像心灵能忘掉所发生的一切,无论什么重要之事。同样,人们能确切地把某些事记忆为发生了的,即使它并没有发生。”
在印度的观念中,没有什么“现实的事件”,人的精神在梦中,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事件,对他的精神来说,是的确发生了。而且不同的人的精神意识或心灵中会出现同一个事件,仿佛大家同做一个梦,这种情况下大家就都认为这种事是发生过的真事而不是虚幻的梦。这种观点显然不是唯物主义的。
印度人的这种观点,在中国不是主流,只有庄子曾有过,庄子说:“我曾梦见自己是蝴蝶,醒来后想,是庄周做梦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成了庄周呢。”另一个印度人讲的梦故事仿佛正是为了回答庄周而讲的:
从前,有个喜欢想象千奇百怪的事情的僧侣。他所有时间都在冥思苦想,岁月飞快地逝去了。一天,一个幻念忽然袭击了他:“真有趣,我将经历发生在初民身上的事情。”他一有了这念头,他便莫名其妙地换上了另外一个人的模样,那人的身份和姓名,即使这只是精神造成的。由于纯粹偶然的事件,当一只乌鸦碰巧在树下,一颗棕树的果子掉下来刚好打在他头上时,他想:“我是吉婆陀。”这位梦者吉婆陀在一个梦构成的城镇里尽情地享乐了很长时问。他在那里喝得大多,倒下来沉重地睡着了,他在梦里看见一个整天读着什么的婆罗门,一天,那婆罗门躺下睡着了,整日的劳作使他很困倦,但那些日常活动仍然使他显得有活力。同样如此,在梦中他把自己看成了王子。一天,那位王子在饱食肉宴后睡着了,在梦中他把自己看作统治着宽广领地的穷奢极欲的国王。一天这位国工因为狼吞虎咽。纵情享乐而睡去了。在梦中他把自己看作是位仙女,这位仙女固连续的作爱的困倦而睡去了,她在梦里把自己看作一只有闪亮眼睛的雌鹿。一夭雌鹿睡着了,她梦见她是株葡萄藤,因为她从来就喜欢吃葡萄;就动物而言,它们总是记得它们所见所闻的东西。葡萄藤把自己看作在藤上酿蜜的蜜蜂;蜜蜂在莲塘里爱上了莲花/一天,官变得如此地沉醉子所仗用的莲汁,以致它的头脑都麻木了,正在此时,一头象来到塘边,踏翻了莲丛,仍然依附在莲上的蜜蜂被压挤而到了象牙上。当蜜蜂瞧着大象时,它把自己看成了发情期的大象,大象掉入了一个很深的陷阱,成了一头令人喜爱的王室的象。一天,象在战斗中被利剑砍咸了碎片,当它走向它最终的慈息之地时,它看见一群蜜蜂萦绕在从它的头脑上流出的甜美的血液上,于是象再变成了蜜蜂,蜜蜂又回到了莲塘,被踏在象脚下,这时它看到了池塘中它旁边的一只鹅。于是它变成了鹅。这只鹉在一段长时问里经历了数次再生,直到一夭,当它是一群鹅中的一只时,它熟悉到,作为一只鹅,它类似于梵天的天鹅,类似于造物主的天鹅,它一旦有了这念头,它被猎人射中死去了,于是,它再生为梵天的天鹅。
一天,天鹅见到了楼陀罗神,突如其来地,它想到:
“我是楼陀罗。”这个念头马上像镜中的意象一样反射出来了,它换了楼陀罗的模样。这位楼陀罗沉溺于他精神的每一种快乐,他生活在楼陀罗的宫殿,备受楼陀罗的仆人照料。
但是,这个变化而咸的搂陀罗有一种非凡的熟悉力,他的精神能看到他先前的每一个经历。他惊奇地看到他做了1oo个梦,他自言自语道:“多奇妙啊!这个复杂的幻觉愚弄了众人;非真实之物似乎是真实的,就像终归是幻境的沙漠中的水。我是某些能被想到的某物,我被想到过。在这里偶然碰巧地,在某个宇宙中有个变成了憎侣的灵魂,他经历了他所想要经历的东西:也变成了吉婆陀。但因为吉婆陀欣羡婆罗门,他把自己看作了婆罗门;因为婆罗门总是想当王子,他变成了王子。因为王子为了治理王国而想干番事业,他变成了国王;因为国王想满足淫欲,他变咸了仙女。变幻无常的仙女大妒忌雌鹿漂亮的眼睛了,她变成了雌鹿;雌鹿把自己看作她关注的依附男人的女子,女子把自己看作她观察了相当长时间的蜜蜂,蜜蜂被踩在他所看到了的大象的脚下,他时隐时现地经历了一系列的再生。一百次循环再生的结局是楼陀罗,我是搂陀罗,我是他。他站在再生的潮流中,在那里众人被他的精神所耍弄。就我的爱好而言,我要唤醒所有那些是我的再生的造物,我要观察他们,给予他们真正观测事物的能力,我要使他们联合为一。”
楼陀罗下了这个决心,他去了那个僧侣正像死尸般睡在寺院里的庙字。把他的精神投入僧侣的心灵后,楼陀罗使他醒来了;于是,僧侣熟悉到了他所产生的错误(即相信他的吉婆陀那样的生活是真实的)。当僧侣瞧着搂陀罗时,发现楼陀罗本是僧侣,也是吉婆陀及其他人造成的,他大为惊愕,尽管那个真正醒悟了的人没有发现他惊愕的原因。于是,楼陀罗和僧侣两人一块去了吉婆陀再生的精神角落的某个确实的地方,于是他们看见了吉婆陀睡在那里,毫无意义,手中还握着剑;那是吉婆陀的尸体。当他们的精神熔入他的心灵后,他们使他醒来了,于是,虽然他们是一个,但他们有三个形式:楼陀罗、吉姿陀和僧侣。虽然他们醒着,但又似乎没有醒;他们很惊异,然而又不惊异,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那里,像画在画片上的意象。
然后,他们三人在空中互相回应,飞越天空去了个地方,那是婆罗门的再生之地,他们在他家里看到了婆罗门,他与他妻子睡着了,他妻子用手挽住他的脖子。他们把他们的精神溶入了他的心灵,使他醒来了,他们全站在那里,不胜惊奇。然后他们去了国王再生的地方,他们用他们的精神唤醒了他,然后他们又漫游于其他人的再生地,直到他们到达了梵天的天鹅的再生处,在那时他们全联合起来了,变成了楼陀罗,一百个楼陀罗变成了一个。
于是,他们都被楼陀罗唤醒了,他们都欣喜兴奋,彼此观看他们的再生,观看如此发生的幻觉。然后,楼陀罗说:
“现在,回到你们的位置上去吧,在那里与你们的家庭共享欢乐吧,到时再到我这里来。到世界未日,我们所有人的,这帮无非是我的部分的造物都将走向最后的慈息之地。”于是,楼陀罗消失了,吉婆陀。婆罗门及所有其他的人都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与家人团聚,但一段时间后,他们将耗尽他们的体力,重新回来在楼陀罗的世界里团聚。
由引可见,印度人对梦的看法是最神秘的,他们认为世界就是梦。而梦中的一个人的精神可以转化或分解为几个不同的精神。这些不同的精神之间又是同一的又是独立的。这种观点比中国古人认为人睡后有一个灵魂出窍形成梦或鬼神致梦显然要奇异得多,神秘得多。
文章来自♀,未经允许♀不得♀转载!